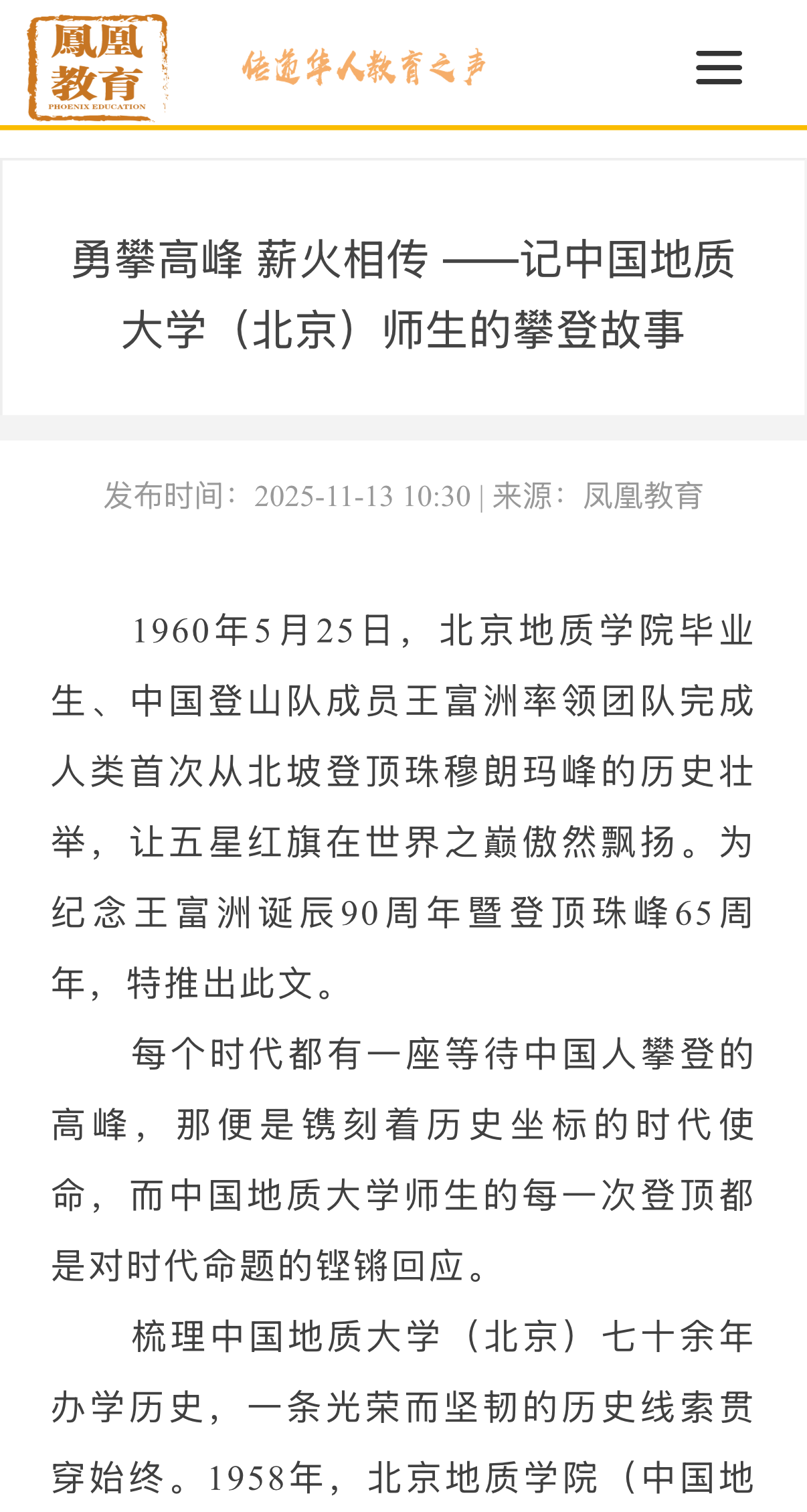
1960年5月25日,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生、中国登山队成员王富洲率领团队完成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历史壮举,让五星红旗在世界之巅傲然飘扬。为纪念王富洲诞辰90周年暨登顶珠峰65周年,特推出此文。
每个时代都有一座等待中国人攀登的高峰,那便是镌刻着历史坐标的时代使命,而中国地质大学师生的每一次登顶都是对时代命题的铿锵回应。
梳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七十余年办学历史,一条光荣而坚韧的历史线索贯穿始终。1958年,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成立了中国第一支业余登山队。1960年,地大毕业生王富洲参加中国登山队,从北坡登上了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同年,学校登山队8人沿东北坡首次登上青海阿尼玛卿Ⅱ峰,首次揭开了阿尼玛卿雪山的面纱。1996年,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建成北京高校首座专业攀岩场地,次年率先将攀岩课程纳入本科教学体系,开创了国内高校户外教育的先河,目前已形成包含《攀岩运动》《定向运动》《野外生存》《户外运动》《拓展训练》等户外运动课程群。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党委书记雷涯邻说,地大学子七十余载踏遍群峰的足迹昭示,真正的攀登不仅是征服自然高度,更是以“攀登精神”破解发展难题,将个人奋斗的足迹铭刻在民族复兴的等高线上。当每个时代的开拓者将使命铸入登顶之路,人类文明的旗帜便能永远飘扬在崭新的高度。
那个年代,这个成绩是要用生命和鲜血去换的,其中可歌可泣的事迹难以用几句话来表达。但在世界最高峰顶刻上中国人的印记,我们无怨无悔。——王富洲

1954年9月,出生于河南省西华县一个农民家庭的我,带着全村父老的厚望,来到北京地质学院就读石油及天然气地质专业。1960年5月25日,这是我终身不忘的日子,我参加了中国登山队,从北坡登上了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
中国登山队的这一创举,完成了过去认为人类无法完成的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艰巨使命,震惊了世界。追忆这段经历不胜感慨,如果没有当年老师和领导的辛苦培养、关怀和谆谆教诲,就没有这一荣誉的取得。
4年的大学生活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严正的校风,师生之间的团结友爱,老师们诲人不倦、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育人风范。学校领导非常重视对我们的思想教育,当时的地质部何长工副部长经常来学校给我们作报告,讲光荣的革命传统,讲地质科学工作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勉励同学们努力学习马列知识,认真学习科学文化,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毕业分配时,我们都不留恋安逸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强烈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被分配到国家体委的中国登山队,并作为突击组组长和主力队员贡布、屈银华两位同志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峰。那个年代,这个成绩是要用生命和鲜血去换的,其中可歌可泣的事迹难以用几句话来表达。但在世界最高峰顶刻上中国人的印记,我们无怨无悔。
每天除了上课、实习和下午一个小时的体育锻炼外,学校时不时还有各种各样的义务劳动,文体活动、球类比赛等,我们在德智体方面得到较全面提高,较好地培养了不畏艰险的团队精神,树立了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坚强意志。——袁扬

在北京地质学院学习的四年(1952-1956),是非常紧张愉快、丰富多彩的。我对山的情怀始于母校,每年野外实习都离不开爬山。野外实习既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也是我与大山结缘的机遇。在温泉城子山的测量实习中、周口店的地质实习中、在房山地质标本采集中,以及山东泗水、平邑等地的生产实习中,攀登穿越山山水水都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记。
1953年暑假,我们在房山采集教学用的岩石标本。一天下午,刚完成预定采集任务,眼看大片黑云快速从远方飘过来,霎时倾盆暴雨接踵而至,未几山洪暴发,泥沙翻滚奔腾而来,趟水过河的归途近道被洪水切断。不得已只好翻山越岭绕道过桥。一路上大雨滂沱,平时乡间小路已成小溪,我们七、八个同学手拉手靠集体力量奋力拼搏,闯过了多处危险地段,一群“落汤鸡”饥寒交迫,在漆黑的夜幕下总算到达周口村。少年情怀都是诗,大家在村头小饭馆狼吞虎咽美美饱餐一顿,夜半才兴高采烈地奔向宿营地。
1956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为了有较扎实的专业基础,一年后我回到母校普地教研室进修第四纪地质。1958年我国组建登山队准备攀登珠穆朗玛峰。这时,我萌发了随登山队进山,探索3000万年来正在迅速隆升成为世界屋脊地区的第四纪地质设想。于是向高等教育部提出申请,经批准参加了登山活动。经过登山训练班的学习,我先后参加了由国家组织的一些重要登山活动如:1958年秋攀登苏联列宁峰活动;1959年攀登慕士塔格山活动;1960年攀登珠穆朗玛活动,其中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三人首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1961年登公格尔九别峰攀登活动,破女子登山高度世界纪录。当你艰辛穿越陡峭冰坡,攀越冰壁,沿鳍脊登上高山之巅,鸟瞰四周清幽苍茫的群山时,你多会完全忘却刚才攀爬的艰辛与危险,油然而生出那种天地人合一的感受,这也许正是它吸引那么多人去探险的原因。
最大限度地将地大的登山精神传递给每一个人。不管时代如何发展,我们毅然行走在攀登的路上,为站上世界之巅的目标不懈努力。——邓军文

1987年大学毕业后,我就来到北地体育部当老师。这一年正赶上我国攀岩运动刚刚起步,我开始接触攀岩,成为继中国登山协会专业教练之后的首批攀岩运动员和攀岩教师。1990年我开始带学生当教练,并开始在中国登山协会组织的攀岩赛事当裁判和做组织协调工作。
1996年,我校建成了北京高校第一个攀岩场地,第二年正式为本科生开设了攀岩课程,攀岩教学和训练占据了我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我也从攀岩竞技场的舞台走向了幕后。幸运的是,我收获颇多:我带出来的女队员中,慕煜、李云霞有着“攀岩姊妹花"的美称;男队员中,徐宏波在1999年全国攀岩锦标赛上取得了难度赛和速度赛的双冠王,与丁祥华、李文茂、赵雷并称中国攀岩“四大金刚”。
攀岩运动是从登山运动派生出来的,与中国登山协会的登山家接触多了,攀登雪山成了我的心愿。在成功登顶慕士塔格峰后,重建地大登山队的想法在我心里萌生,如何发扬地大登山优良传统,传承登山精神,成了我教学训练之余的思考。2007年,在全面了解登山运动的精髓之后,我鼓足勇气向学校和有关部门写了关于恢复地大登山队的申请。2008年,重建地大登山队获得批准。同年10月,我亲自带领学生奔赴云南哈巴雪山,最终实现了10人成功登顶。
如今,登山队已更名为大地社,为了让更多学生体验到户外之美,除了传统的攀登雪山活动,每年冬季还会邀请全国高校户外社团到北京天池峡谷和玉渡山开展大学生冬训营,教授攀冰、岩降、雪坡行走以及绳索技术等。暑期进行骑行、科考、支教等社会实践活动,活动轨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最大限度地将地大的登山精神传递给每一个人。不管时代如何发展,我们毅然行走在攀登的路上,为站上世界之巅的目标不懈努力。
地大有太多特别之处,在这里我们建立了“地球视野”,以地球科学的视角来观察世界,这是一种情怀,一种穿越时空的浪漫。——温旭

2019年11月到2020年1月,我从南极大陆的海岸出发,以越野滑雪的方式,历经58天,走了1500公里,到达了南极极点,创造了单人无助力徒步南极点最远距离的世界纪录,也是一项欧美人也没有完成过的挑战。在南极,一个人孤独地顶着令人窒息的压力和各种困难,在地球最极限的环境下,用科学探险向世界展现一个中国青年探索自然的勇气和坚持。我希望通过行动去呼吁人类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冰川,希望在构建人类与地球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贡献力量承担责任。
我是2007年走进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校门。本科期间,我在学校师长们的支持下重新组建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登山队及大地社。初创三年,我们攀登了14座雪山,并在2012年代表母校攀登珠穆朗玛峰。硕士阶段,我开始了第四纪地质冰川方向的学习,一年里有半年都在青藏高原。从冰川中探知地球气候的演变历史,让我加深了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注。
地大的攀登精神、探索精神深深地刻印在我的灵魂。在雪山之巅、地球之极,当我看到冰川在全球升温的背景下日渐脆弱,在探究了青藏高原的冰川和气候环境变化之后,我决定穿越地球的三极,去看看地球的系统性变化。我准备了两年时间,期间有很多国内国外的质疑,一个年纪轻轻的中国小伙可以完成这样的挑战吗?那时候,我已经毕业5年,但我又重新回到地大的操场上,在这完成了体能集训、模拟训练。母校还支持我,在报告厅举办了出征仪式。
地大人奋斗在人类探索自然的第一线。在这里随便研究的一块岩石,一个褶皱断层、一个地质地貌,它的形成都是以百万年为时间尺度,超出了人类的文明发展历程,包含了地球46亿年乃至更广阔时空的精彩故事。在我心里,地大有太多特别之处。在这里,我们建立了“地球视野”,以地球科学的视角来观察世界。这是一种情怀,一种穿越时空的浪漫。
作为2020年珠峰最新高度公布后首位北坡登顶者,我于10时50分抵达峰顶后立即开展科考:架设北斗RTK定位设备、采集冰雪岩样。经过近60分钟高寒缺氧作业,最终在世界之巅完成了北斗系统实测,用测绘人特有的方式丈量祖国山河。——陈李昊

我来自湖北武汉,2020年怀揣着对地球科学的向往考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测绘工程专业。四年间,我在课堂里汲取知识,在攀岩场与定向越野中锤炼意志,更在登山科考的实践中触摸到测绘人“丈量山河”的使命——这段交织着汗水与星光的成长历程,最终将我推向了世界之巅。
邓军文教授的《野外生存》课程始终镌刻在我记忆深处。邓老师给我们系统讲授户外运动发展史与生存技能,组织我们深入山野开展实践教学,更通过讲述我校登山前辈勇攀高峰的事迹,将“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登山精神深植我们心间。那些在篝火旁聆听雪山故事的夜晚,悄然点燃了我“将科研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理想。
2022年4月30日,我以地大学子身份从北坡成功登顶珠峰。作为2020年珠峰最新高度公布后首位北坡登顶者,我于10时50分抵达峰顶后立即开展科考:架设北斗RTK定位设备、采集冰雪岩样。经过近60分钟高寒缺氧作业,最终在世界之巅完成了北斗系统实测,用测绘人特有的方式丈量祖国山河。
回首这段攀登历程,我深深懂得:峰顶飘扬的校旗背后,是导师们课堂上的谆谆教诲,是登山队前辈的技术传承,是“艰苦朴素、求真务实”校训的精神指引。这份荣光,永远属于培养我的母校与师长。
(通讯作者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党委宣传部 唐旭 董婷)